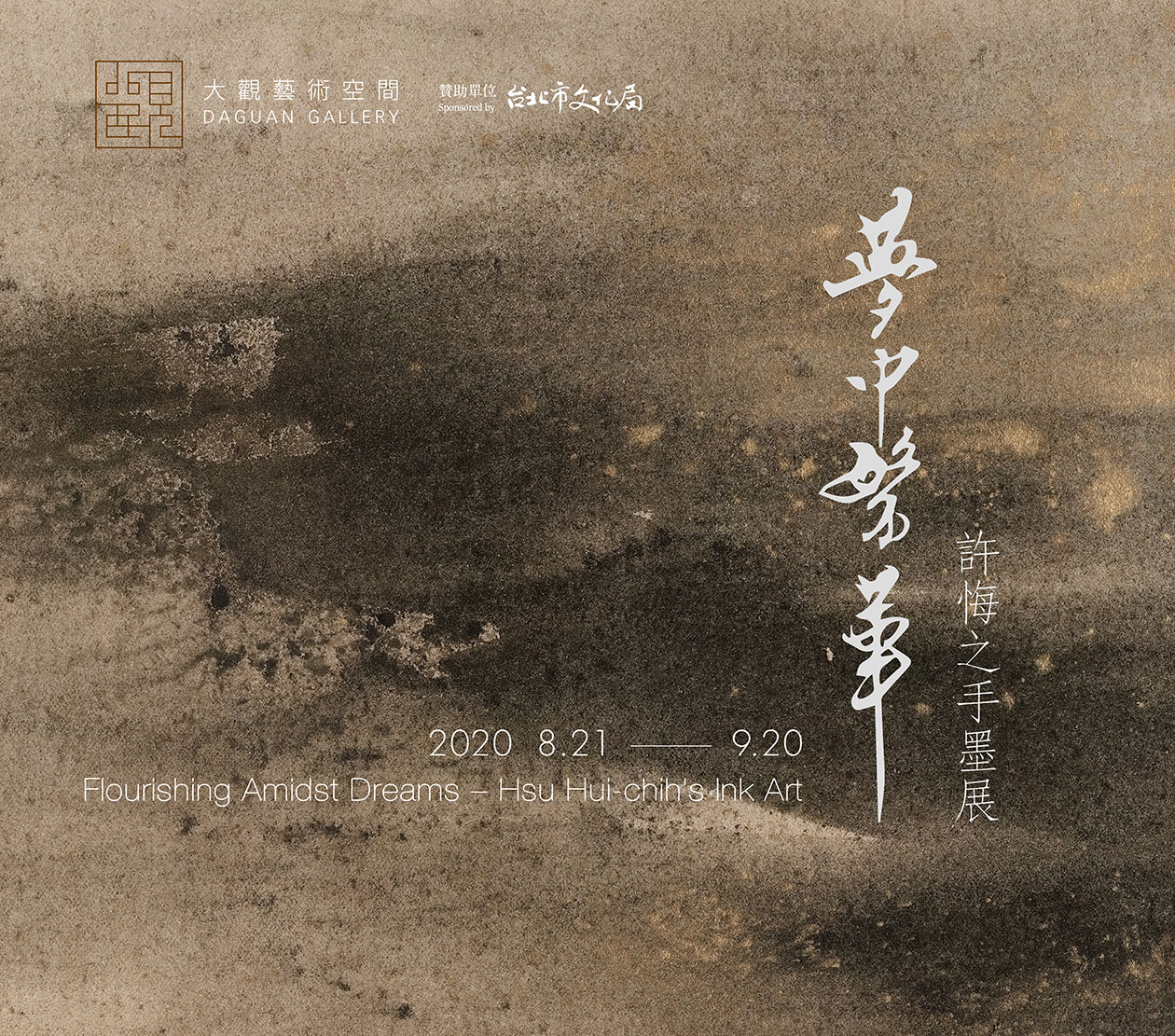林欽賢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美術系專任教授、美術學系系主任
那年油畫課的班上來了一個轉學生,即使特別安靜,但仍然很容易地被注意到。我對他的來意感到好奇,而他的好奇卻逐步展現在對藝術的追求。藉由談論顏群〈千分之一風景〉,針對如此精妙的命題與藝術旨趣,今天的我很高興有機會來分享自己一些觀察心得與對人類心靈的樂觀。
美術史學者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所撰寫的經典風景繪畫史“Landscape into Art”,國內學者廖新田譯為《風景入藝》,描述了自然景觀作為畫家唯一觀想對象的歷史脈絡。以西方經驗而言,那可以說是一個有關城市人為擺脫文明而藉藝術語言以展現特定自然史的故事。或者,現在的我們,也不難從閱讀數千年前的《詩經》而察覺到人類的心靈世界是多麼地與自然緊密連結,以致那蟲鳴鳥叫都能呼應尋找愛情的人們其內心最原始的悸動。自然,一直都包圍著我們,只是現今的制度讓大家幾乎都沒有選擇餘地得去追逐文明所定義的成就,人們視界中植物所佔的百分比理所當然的稀少了。所幸,顏群現在所做的,和歷代的風景畫家一樣,逐步要開啟綠色世界的奧秘,揭露一個平時被我們所忽略的視角。
理性的感性形式
以我對顏群的認識,似乎很自然地必須談談他美學中的理性價值,說說他如何將藝術修辭法中的感官刺激性降低到一種水平,接著才是我讚美這〈千分之一風景〉其感性魅力的時刻。
我想,簡單地說,有兩種視角會幫助人們更容易地看到平常環境的不平常,或不規則世界中的規則:一個是巨觀的(Macroscopic),另一個是微觀的(Microscopic),而顏群將自己的眼睛固定在剛好可以清楚觀察葉片生長軌跡的距離,我說那個視角是一個引領畫家的視覺進入到「幾何思考」的界線,這是一種微觀方式,卻也是一種巨觀的心態;這時植物的綠色尚且不致被過度解構,同時莖葉的紋理與線條也表現出幾何學上的角度關係,與基本構造上的數學原型,同時也體現植物色彩上的恆常性,一種省略許多環境變數下的生命溫度;因此,這讓我想起達文西總是鎮重地向著友人訴說解剖一具人體時,需要多大程度的冷靜、理性與細膩,才能在模糊血肉中整理、繪製出真實又有調理的解剖學素描。
我想,〈千分之一風景〉所呈現的規則線條與植物的恆常色彩,是藝術家為了印證其生活理念的方法學吧,無法確切得知作者基於什麼樣的成長經驗而想藉描寫植物來暗示世界運行的理則,但是我還是感受到抽象的音樂性在「顏氏美學」中的重要程度,當他在進行這些抽象的數學成分之圖像操弄時,感覺他將大量心思投入在二維世界之「線與面」的豐富變化中,企圖譜寫出如〈田園交響曲〉一般的壯碩旋律,而這旋律僅僅是由幾個簡單的音符所構築而成。
根據顏群的說法,相對於動物的世界生命型態,那是一種所謂植物被動於環境限制下所表現出的特有生命特徵,一種能默默等待機會而服從宿命的,卻也竭力享有陽光、空氣、水……的樂觀積極。
顏氏綠
我們知道有所謂的凡戴克棕、委拉茲圭茲紅,這些詞彙其實都是來自世人對大師們一種讚頌,無論是針對其作品獨到的色彩協調性,或是掌握到一種色料的絕妙應用之道,甚至是由於他們引發潮流的現象,人們都相信大畫家是色彩的魔術師。而不知從何時起,顏群開發出了自己一套的綠色諧調法則,而我覺得,他已經很熟練地將陽光的熱情過濾成冷靜的溫柔,我恣意將他的這種低溫的綠色稱為「顏氏綠」。
林布蘭通常習慣以單色底色畫法來構築一幅畫的初始圖像結構,主要是在造形、明暗關係上下足功夫到一種滿意的程度方才停止底色畫的任務,他自己稱這個階段是「死的色彩」(dead color),不曉得他的油畫經過多少次的色彩薄塗與罩染後,作品才從「死」的狀態中活出來,畫面上開始照耀在神秘的聖光之下,依照大師的標準,作品自始能夠呼吸。我感覺到顏群也應用類似的方法來做油畫創作,然而他卻非常有節制地使用表現陽光的黃色系顏料,反而將灰與藍作為他塑造綠意的基本元素,或許,他覺得,與其像印象派或梵谷那樣熱情地讚頌光合作用,不仿也歌詠「葉綠素」本身,畢竟這元素是一個星球展現生命的關鍵吧。
我相信,藝術家像是敏感的天線,只是他或她總是在尋找屬於自己獨特而專有的頻道,一個與自身的「生命圖譜」相互唱和的「波」,這是一個只有他或她才有那把「金鑰」以開啟進入這頻道的空間,而一旦尋找到時,就像是如魚得水般地藉著這個頻率來做無限創造,不僅開啟了自己的藝術生命,同時也開始與這婆娑世界進行深邃的對話,現在的顏群,我想,似乎已經掌握了那個波段。
...